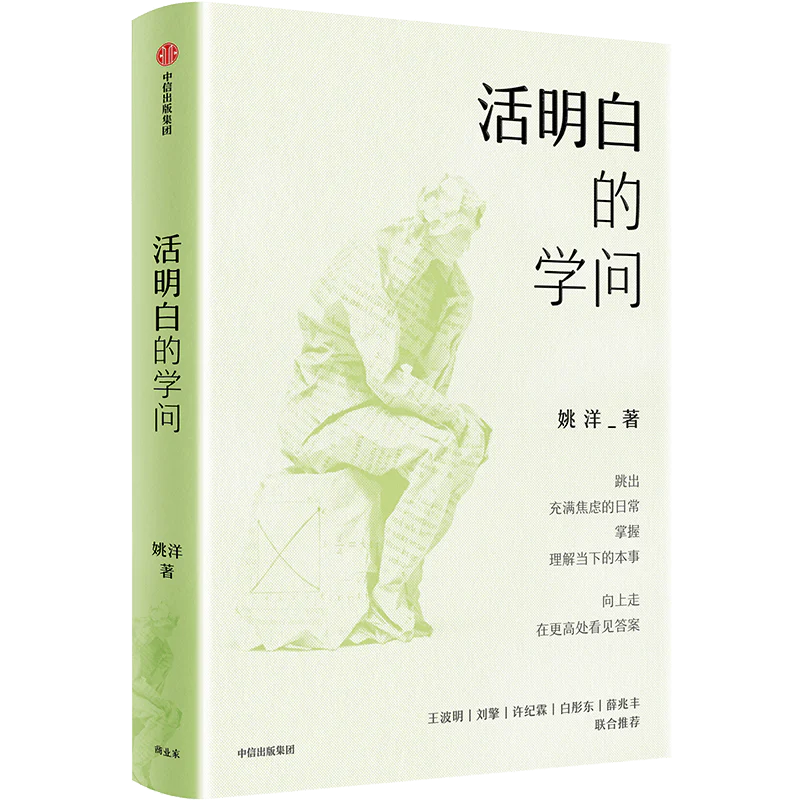FIRST创投15年,在迷雾中踩出路径。
15年的时间能做什么?
按照著名的“一万小时定律”,只要每天投入2小时,15年后就能达到10920小时,一个平平无奇的普通人就能成为一个专家型的人才。
对于中国电影来说,这十五年里,有一件事从无到有,慢慢生长,那就是电影创投。虽然不比西方历史悠久的电影节从上个世纪80年代便已经有了创投雏形,但在国内的电影节中,FIRST是最早组织创投的电影节之一。
十五年里,FIRST像一个沉默的陪伴者,看着一代代青年电影人带着他们的故事走来,也见证了整个行业的热情与冷却、困惑与求索。不过,这十五年,并非一路高歌猛进,更像是在迷雾中一步步踩出路径。我们不禁想问:这条路走了这么久,它的尽头,究竟会有什么?
风起于青萍之末
如果算上创投的前身,故事的起点应该从2010年说起。
那一年,中国电影票房突破百亿的成绩,唤醒了许多青年导演的电影梦。在北京华北电力大学的报告厅,一位即将迈入而立之年的导演,顶着一头文艺青年标志性长发站在了“新青年导演”项目推介会的舞台上,台下坐着的评委是徐峥、苏有朋以及不超过15家电影公司。
后来的他剪去了长发,合作上了成龙,拍出了人生第一个破10亿的电影《捕风捉影》,15年前的那一刻,是杨子的起点,也是后来太多青年导演的起点。
彼时的那场活动,还叫“新青年导演”项目推介会,报名系统都不完善,差不多有10家公司都是FIRST创始人宋文一个一个联系的。但是,一个此后在全国遍地开花的青年影人入行“必修课”就这样有了雏形。
那一年的FIRST还不叫FIRST,也不完全是大家耳熟的前身“大学生影像节”,而是在前面加上了“国际”二字——因为那是影展第一年开启国际选片。次年,FIRST正式落户西宁,成为了现在大家所熟知的FIRST青年电影展。夹在新旧之交处,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草莽力量正在暗流涌动
“新青年导演”项目推介会流程和现在的创投大相径庭,处处透露着生涩。因为是在学校的报告厅,评委和创作者分坐在台上台下的长条桌子后面,给人一种开报告会的感觉。而每位创作者也没准备完整的剧本,只是上去阐述自己脑海中的故事,力求让场下的行业前辈产生一丝兴趣。
尽管这只是一次非常粗糙的尝试,但行业反响还不错,这坚定了宋文的想法,电影创投是一件必须坚持做下去的事。
做影展之前,宋文在IDG投资公司上班,当时IDG投资了A-G艺术院线,并发行了一些艺术电影,“我当时的感受非常模糊,我只是觉得我们应该有非常专业的公司和非常专业的作者,然后在一个专业的环境下去讨论电影,并且是高效的。”
那几年,宋文开始频繁参访国际电影节展,构思如何在国内落地具有相似行业功能的节展环节。2010年,宋文去了瑞士洛迦诺电影节的全球电影人训练营,第一次参访海外节展给了他极大的刺激,“好像那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场景,它有一个近万人的巨大露天放映广场,也有很多针对新导演的program,包括餐厅之类,我能感受到浓烈的电影节文化氛围。”
形成一种良好的氛围,非旦夕之功。宋文希望有一天国内也能有一个“所有做电影的人能够高效讨论”的场域,但具体形式、规则是什么样的,他暂时还不明朗。
2011年,创投的名字改叫“拍谁计划”,呼应当时FIRST的奖杯“荣誉板砖”。直到2013年,变成了现在的名字,也是在那一年,FIRST创投会开始有了提案(Pitch)环节。
由于此前国内缺乏创投基础,很多青年导演对创投根本没有概念,需要从头开始培训。FIRST在训练营的课程中专门加入了关于提案的培训,宋文决定亲自上阵,“我们在橙天嘉禾影城的VIP厅外面做培训,里面在放电影,外面有一个独立的小空间,我们就在那上课,声音还不敢太大不然会吵到里面的观众。”宋文回忆当时场景。
但即便经过了简单培训,创作者依旧是稚嫩的。由于并没有完整剧本作为参考,评委只能聆听创作者的陈述来给出意见,2013年坐在台下的导演谢飞直言,“听得不是很明白,如果作为导演在阐述自己的故事时都没有明确的主谓宾的概念,是非观模糊,讲一个不知所云且随波逐流的故事,很难想象如何把它变成人人都能看懂的电影。”
不善表达,其实是早期不少年轻电影人的一大共性,学习于艺术类院校的他们,少有在多人公开场合演讲的经历,多是习惯躲在影像的舒适区里。而这是在FIRST看来,职业导演的必需技能,是需要倾注力量帮助年轻创作者提升的核心能力。“当然有的导演确实比较内向一些,有的天才型导演也并不需要,依然可以把电影做得很好,但那终究是凤毛麟角。普遍意义上来说,电影导演就是一个需要在公开场合下,去充分阐释个人创作意图的工种。”宋文表示。
写完剧本天黑了
无论采用怎样的形式,真正支撑创投的地基从来只有一个——电影公司押宝新人的热情。每当有现象级作品或影人从创投中出现之后,这股热情就会势不可挡地被放大。
国内创投遍地开花的第一股热潮,在2016年出现了。那一年的FIRST创投会有胡波的《大象席地而坐》(原名《金羊毛》)、周子陽的《老兽》(原名《老混蛋》)、翟义祥的《马赛克少女》等等,是当之无愧的“创投大年”。彼时正值中国电影市场迈入“后400亿”票房时代,资本对影视行业前景普遍乐观,大量热钱涌入的背后,是市场对优质内容、对新导演与新项目的巨大渴求,渴望复制下一个票房奇迹或行业标杆。
《长夜将尽》的导演、编剧王通,正好迎面撞上了这股热浪。从早期在FIRST做志愿者,到2025年《长夜将尽》入围FIRST主竞赛,并拿下最佳演员和最佳编剧奖,王通是少有几乎参与到了FIRST每一个板块中的创作者。
2010年还在传媒大学读书的时候,王通就在大学生影像节的选片阶段看过片。2011年改名FIRST落地西宁之后,他迅即参加了训练营,那时的训练营还不像现在这样有拍片的机会,是一系列课程讲座。到了研究生阶段,王通推动自己供职的朝阳文化馆开辟艺术影院,成为FIRST的线下放映场景。快毕业的时候,王通拍了自己的毕业短片《吉日安葬》,当中的演员也是通过FIRST联系到的,也是那一次,王通决定将自己的毕业短片投递到FIRST
日后,王通回忆,恰恰是因为迈出了投递FIRST的第一步,后来不断有人启发他,也可以给更多国际影展投递,才有了他后来在釜山国际电影节入围的机遇。
那次投递后,并不是王通与FIRST机缘的终结,反而让他的人生走入新的境遇。很早就立志要做职业导演的王通,开始构思自己的长片故事,也慢慢了解到创投这个渠道。2016年,王通参加了首届要求进行拍摄实践的全新FIRST训练营,他将长片故事浓缩成了一个短片剧本,就是《长夜将至》最早的故事雏形。在训练营期间,王通又写出了长片的2000字剧本大纲,这让他拥有了2017年创投的敲门砖。
彼时的创投还不需要拥有完整剧本,仅需要提供剧本大纲,评委和创作者沟通时只能根据大纲和过往资料来聊,而王通却直接有了一部比较类型化的短片作为demo,“那几年国内创作者受韩国电影启发很大,那部短片看着又有点儿‘韩范儿’,更‘唬人’了。”
在市场最火热的时候奉上类型化的剧本,王通享受到了理所应当的“追捧”。他感觉到那年投资人的热情非常高涨,来西宁的电影公司很多,预约洽谈是完全爆满的状态。事后回忆,王通觉得当时的火热也给自己传递了一种假象:“我原来老觉得自己闷头把剧本写好就行了,因为我觉得剧本最重要,自己什么时候剧本拿得出手了,就一定能够找到钱拍片。”
但因为参与创投的时候还没有创作出完整剧本,许多感兴趣的投资人都停留在“期待剧本”的阶段。而当王通终于写出完整剧本时已经是2018年底,一切沧海桑田,王通像“烂柯人”一样发现外面“天黑了”,“早期跟我联络的那些人可能都忘记这个事情了,再跟人联系的时候,很多人都已经不在原来的公司了。”
在宋文眼中,这其实是不少创投团队在“跟踪率”上存在的结构性问题。“跟踪率”指的是创投项目开发阶段的制片人,跟踪潜在投资公司的效率管理。“如果说你的文本在市场上接触过一两轮之后,理论上应该要跟住那些谈得比较好的公司了。但现实情况是,创投链条上下游容易松散,会发生制片人过段时间被换掉了,或者导演一直埋头写剧本诸如此类的情况,慢慢就没有人去跟踪这个事了。”
回顾那段旅程,王通认为创投对他最大的帮助是,在跟他人一次次地讲述这个故事的过程中,发现自己还是很想写这么一个人物,“这其实也是我这么多年能把这个项目坚持下来的动力之一吧。”
从同质化中突围
紧张地喝了几口白酒,因为怕在舞台上摔倒,她索性光着脚上台介绍了自己的项目。那是
2020年的FIRST创投会始终会被记忆的一个瞬间,主角是邵艺辉和她的首部惊艳行业的作品《爱情神话》。这一年的创投,理所应当地成为了又一个分水岭。
在宋文的记忆中,从这一年开始,媒体与业界开始普遍地对创投有了一种反思,“大家普遍对创投感受到一种疲惫感,而这种疲惫的本质就是同质化。”
有的项目一年可能跑遍所有创投;有的创作者换好几个不同的项目反复参与但最终还是没有一个被拍出来;即便是不同创作者的不同项目之间,有时也会有强烈的“即视感”;坐在下面聆听的评审和资方代表来来回回也是熟悉的面孔……这些都是创投同质化的若干侧面。
这种现象的产生,首先当然有影展自身的结构性问题。电影节之间或因城市的差异、品牌定位的差异、商业化属性的差异而有所区隔,但各个电影节的创投之间,实际上差异很小。宋文感慨,“行业一直缺乏一个大家一起坐下来聊的机会,很少一起进行意见交换、反思,都是在各自闷头干。”
但从创作者自身而言,也不乏原因。“在2016年前后市场特别好的时候,好像大家也不去讨论电影的创作诚意。实际上我是觉得整体的下坡可能跟很多项目也缺乏诚意有关系。”这个诚意,在宋文看来是创作者对社会现实的同理心、对笔下角色的同情心,“那种来自特别真实情感的文本越来越少,这或许是社会情绪所导致的。大家都是在做一种所谓的‘极致类型化’的尝试,所以会有似曾相识的感受。”
这也是最近几年,FIRST有意识地在惊喜影展中加入跨界嘉宾的核心原因。“我们去请一些运动员、科学家、学者、作家过来,就是因为我们或许有很厉害的导演或者编剧,但是有生命体验的文本在变少。我们愿意用多种方式去刺激那些想法去呈现出来。”宋文表示。
同质化并没有伤害到青年创作者踊跃表达的热情。随着创投数量越来越多,信息壁垒的逐渐降低,新一代的年轻创作者往往有着不少创投履历,即便是第一次参加创投的创作者,也在同行的耳濡目染下对创投有所准备。那种过山车般大起大落的心态,已经越来越少见,大部分创作者对于自己能在创投得到什么有合理的心理预期。
2022年凭借《玻璃动物园》入围创投会的汤琰,在2025年带着自己的新剧本《摩登情书》再次来到西宁。即便只隔三年,汤琰也感觉到市场取向已经大不相同,三年前自己的项目,很难适应如今的市场氛围,“那个作品的气质相对灰暗、边缘,可能不太符合目前市场公司的主流需求,所以我又结合当下的市场情绪写了一个新的剧本。”
在汤琰看来,创投的好处可以用一句话概括——找工作跟老板谈。因许多有决策权的资方领导会亲身来到创投活动上对接年轻创作者,这是在非创投场景中来之不易的机会。而2022年在创投会上建立联系的一些电影公司,这次再来也无需重新了解,减少了不少沟通成本。
“虽然2022年的时候项目拿了奖,洽谈的人也很多,但是它在推进的过程中总是会卡在某个地方。这一次来大家聊得就很实在,不再说‘我对你的项目感兴趣,回去再聊’,而是直接跟我说‘我觉得你这个应该怎么做’。不管之后有没有成功合作,这些建议都是非常宝贵的。”
跑过许多创投的汤琰,对FIRST创投的独特印象在于“对剧本的保密性做得很好”。FIRST创投并不会给参与的电影公司完整剧本,而是等到洽谈环节后,双方有初步合作意愿了,再单独给到完整剧本审看。
为了让创作者有更多被看到的机会,FIRST也试图通过流程创新来优化这一效率。在惊喜影展上,有一个惊喜阅览室环节,只要来过FIRST创投的项目剧本就可以拥有一个长久曝光的机会,资方代表需要亲身到阅览室中去阅读剧本而不能带走。这一环节让汤琰直到现在,还能时不时认识对早期项目感兴趣而添加联系方式的人。
创投应该有什么?
投递、筛选、入围、提案、洽谈……国内每个创投的流程莫不如是。我们都知道创投里面有什么,但我们很少追问创投应该有什么。
早期作为舶来品的创投,学习和借鉴西方模式是题中应有之义。2013年,宋文和同事去访问了圣丹斯电影节,作为历史悠久的“独立电影摇篮”,圣丹斯很早就有了实验室(Lab)的概念。它的实验室会帮助新人创作者分阶段孵化项目,比如像昆汀的首部作品《落水狗》,就是在1991年的圣丹斯电影实验室中,拍了剧本里的两场戏,成片在影展上声名大噪。
实验室的模式在宋文的心里留下深深的印记。FIRST也在很早就开始探索实验室的进行方式。
2016年,FIRST青年电影展与并驰影业共同发起“并驰Lab”,支持从FIRST竞赛体系推选出的青年导演,针对中低成本项目,以院线为目标,从前期项目开发、制作到发行,量体裁衣配置优势资源。2018年,FIRST做了自己的第一期实验室,此后逐渐发展成剧情片实验室、纪录片实验室、制片人实验室等不同方向,《暴裂无声》《两只老虎》《四十四个涩柿子》《不要再见啊,鱼花塘》都是从FISRT实验室中孵化出的代表案例。直到2021年,惊喜影展这个品牌首次亮相,将实验室的属性与惊喜的品牌相绑定,延续至今。
在“并驰Lab”发起的那一年,宋文去了一趟鹿特丹电影节的CineMart,他又看到了创投不一样的形式。CineMart是全球首个电影节创投平台,每年全球遴选30个左右的项目,设置预算的上限门槛,同时必须要有完整的剧本和可以做国际发行的硬性要求。“我印象很深,它在一个类似会议中心的场地里,没有提案环节,有几百家来自欧洲的电影公司,各自在一个洽谈桌前就开始与创作者聊。
2019年在考察完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节之后,FISRT创投又试用了“U形池”的做法。这种形式有点类似商学院,让众多不同身份的评审围坐在U形桌上,还设置了一名类似主持或者法官的角色,去平衡评委、资方和作者之间的关系,在场上根据局势分别帮两边说话。
传统的创投,项目代表上台提案时,可能坐在最后一排的人都在玩手机、交头接耳,沟通效率很低,导致1对1约谈的时候先还得让项目代表又讲一遍项目。而换作U形池之后,所有资方代表都需要更加聚精会神地关注提案过程,并调动自身表达欲。
不过在最终的呈现上,U形池所引发的讨论效果,距离此前的预期还是稍有差距——因为围坐U形池的人数众多,也没有一定要发言的压力。
此外,为了让更多的资方能够同样获得在创投陈述会上发言的权利,还专门设定了一个“热板凳(Hot Seat)”的座位,有3到5个名额提供给“还没到市场合作伙伴属性的公司”,灵活安排一些公司决策者坐在热板凳上,给予点评和帮助。
提案、实验室、洽谈,好像每一个都不是必须存在的流程,但基于惯性,好像每一个又都不好被舍弃。
宋文直到现在也还不能有确切的答案,他仍然在不断思考持续优化创投会的结构。比如他曾构思是否将实验室前置,而创投后置。因为在他看来,在剧本与行业见面之前,其实应该是把大量的工作这些工作先做在前。“因为它还没有到实质的生产阶段,它没有特别大的那种压力,让这些电影能够在实验室这样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下,不断地去突破,然后去讨论电影创作边界性的问题。在这种环境下锤炼出的足够好的剧本再跟大家见面。”
只是如今基于FIRST青年电影展与FIRST惊喜电影展的举办时间,这一动作调整很艰难。它涉及到整个电影节的运作体系,商业模型都要变化。“市场公开周”的形式,是目前一定程度上对实验室功能的补充。它的目的其实就是在正式创投开始之前,先通过一系列的workshop,给剧本一个继续提升的机会,“但还是太短了。”
从2024年开始,“市场公开周”也加入了更多新鲜的模块,比如“模拟研发所”会给创作者模拟电影公司绿灯会的环节,让他们在极限时间内制作项目提案,以达成过会目标。还有“移动实验室”,让创作者能够直接去到各个电影公司上课,在2025年毕赣刚刚从戛纳回来的时候,一群创作者就去到荡麦影业席地而坐聆听他的分享。
宋文能想象到最美好最理想的画面是——把公开周做的工作从一周拉长到十周,把项目尽可能打磨到极限,在AI技术的加持下,连影像预览也有了,此时便不再需要提案陈述,而是可以直接与电影公司洽谈,而此时需要谈的也只是生意了。
遗憾的是,理想的愿景好似总是“镜中月”,现实的琐碎与行业的窠臼总会拖拽着理想与现实的重合速度,但好在,在FIRST打造的“镜中世界”里,理想总是以一种更璀璨、温暖的方式熨帖着所有电影人,最终这些理想也慢慢成了行业里的“鲜花”,我们看到了《暴裂无声》,看到了《爱情神话》……
十五年,创投是一条从荒芜到小径渐显的路。它见证过资本涌入的热潮,也经历着市场进入低谷时的窒息,试图吹散同质化的迷雾。不论那些想法是作者的还是类型的,始终未变的是属于年轻人第一部作品的草莽与真挚。
创投的尽头有什么?在小成本影片如此低迷的市场里,观众到底还需要新人新作吗?答案或许本来也不在终点,而在这个漫长跋涉的过程里,在每一次文本与现实摩擦碰撞、想象与共情交叠演绎的创作里。没人知道未来的电影会走向何方,但它终究会由新的人来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