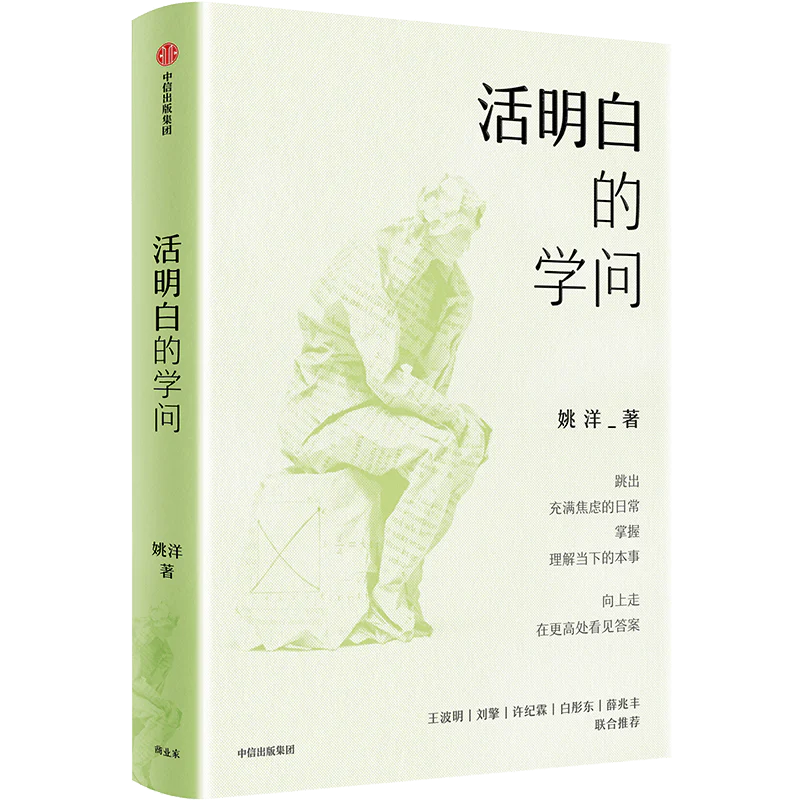
今年,“年轻人报复性挤爆3.5分餐厅”“ AI 续写爽文月入十万”等话题接连刷屏,这是当代人对标准化评价体系的反叛与对新出路的焦灼追寻。当“内卷”与“算法”成为日常,我们是否已在不知不觉中,将自己活成了一串可被优化、亦可能被替代的数据?
当“内卷”从学术概念演变为普遍生存体验
近年来,一系列关于外卖员在交通高峰期为赶超系统限时而闯红灯、甚至引发事故的新闻报道,持续刺激着公众的神经,也将“困在系统里的骑手”这一意象深深烙入社会集体认知之中。这些事件尖锐地揭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现实:在高度数字化的时代,算法不再仅仅是冰冷的程序代码,而是演变为一种塑造、规训乃至支配人类行为的新型权力架构。
然而,倘若我们深入审视便会发现,这种被无形系统“锁定”的状态远非外卖员群体所独有,它实际上已成为现代人一种弥漫性的生存境况。职场人士被关键绩效指标所驱策,在无尽的加班中竞逐着有限的晋升通道;青少年被嵌入以分数为核心的教育竞赛机器,从小学便开始为十几年后的高考积蓄筹码;即便是看似自由的创作者,也难以逃脱流量算法的支配,在迎合平台喜好与保持自我表达之间艰难平衡。我们仿佛都置身于一个庞大而隐形的“全景监狱”之中,虽看不见监视者的目光,却自觉依照某种预期的规范调整自身行为,这种普遍存在的被动处境正是“内卷”现象得以滋生的深层土壤。
“内卷”这一概念在中国学术界的登场,可追溯至历史社会学家黄宗智教授在其经典著作《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对“involution”一词的引入与创造性诠释。这一概念的学术渊源则更早,根植于苏联经济学家恰亚诺夫在《农民经济组织》中提出的“自我剥削”理论。
恰亚诺夫通过细致观察俄国乡村经济发现,在缺乏外部就业选择与市场出路的情况下,小农家庭并不会如经典理论所预测的那样在边际收益低于生存成本时停止劳动投入,反而会持续追加劳动力直至边际产出逼近于零,这种为维系基本生存而被迫向内挤压、榨取自身极限的劳动模式,被他精准地定义为“自我剥削”。黄宗智将这一分析框架应用于华北农村研究,揭示了相似逻辑下的人口过密化与农业内卷化增长。
令人深思的是,一个世纪前发生在俄国与华北乡村的经济逻辑,如今却在高度现代化的中国社会中找到了惊人的回响。当前教育领域的高考竞争便是最典型的例证:各省份顶尖高校的录取名额近乎恒定,构成一个刚性约束。然而,当部分学生选择以“刷题”和延长学习时间作为竞争策略时,便立刻引发了广泛的连锁反应,迫使其余参与者不得不加入这场军备竞赛,最终导致录取分数线逐年攀升,而个体付出的巨额努力却在群体层面相互抵消,未能产生任何额外的社会价值。
这种每个人都理性地选择了对自己最“优”的策略,却共同走向了整体更“劣”结果的困境,正是“内卷”作为一场“囚徒困境”式集体非理性的生动体现,也迫使我们不得不追问:当社会的上升通道日益狭窄且同质化,个体是否除了参与这场无休止的、指向自身的剥削竞赛之外,别无他选?
雇佣关系新解构:从“命令服从”到“平台依附”
2024年初,美团外卖骑手数量突破700万的新闻再度引发社会广泛讨论,这庞大数字的背后,是中国灵活就业人员总量已超过两亿这一深刻的结构性变迁。新冠疫情如同一剂催化剂,极大地加速了劳动力从传统雇佣制向平台化、零工化模式的流转,“灵活就业”已从边缘的、补充性的就业形态,演进为劳动力市场中不可忽视的主流板块之一,这迫使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工作”与“雇佣”的经典定义。
传统的雇佣关系,其核心特征在于它是一种内含权力不对等的命令体系与剩余价值索取权的结合。雇主凭借生产资料所有权,不仅有权支配劳动过程、制定生产规则,更享有在支付所有生产要素报酬及成本后,对最终利润的独占性索取权,同时也承担着经营亏损的最终风险。这种关系将劳动者整合进一个层级化的组织之中,其劳动自主性受到合约与管理的双重约束。
然而,数字平台经济的兴起正在模糊乃至重构这一经典图景。以网约车司机与外卖骑手这两个颇具代表性的平台劳动者群体为例,尽管表面相似,但其劳动过程中的自主性程度却存在本质差异。网约车司机通常享有相对宽松的时间自主权,他们可以依据个人需求或市场状况,灵活决定出车时长与接单策略,其收入与个人选择密切相关;相比之下,外卖骑手则深陷于一套由算法精密编织的控制网络之中,从订单派送、路线规划到送达时限,乃至事后由顾客评价构成的信用体系,无不构成严密的行为规制,一次超时或几个差评便可能触发系统的惩罚机制,甚至导致工作机会的丧失。这种控制不再是传统意义上面对面的监督管理,而是通过数据与算法实现的全流程、自动化、非人格化支配,标志着一种新型“数字泰勒主义”的诞生。
但时代正在发生变化,尤其是在以创新为核心驱动力的高科技领域,传统的雇佣逻辑正在被颠覆。以埃隆·马斯克为代表的创业者,其最大价值并非来自其拥有的巨额资本,而是凝结于其个人身上的超凡愿景、跨界整合能力与技术创新魄力。在这些领域,最关键的生产要素是高度专业化、稀缺且难以被资本直接替代的人力资本。因此,我们看到了一种“劳动雇佣资本”的新范式:顶尖的科学家、工程师或创意人才凭借其不可替代的“知本”,能够吸引风险资本追逐,并在企业中占据主导地位,分享甚至控制剩余索取权。
更广义地看,数字化基础设施的普及,如云计算平台、开源软件、社交媒体和在线市场,为全球个体提供了近乎零边际成本的“虚拟生产资料”。一个人凭借一台电脑和网络连接,便能调用堪比昔日大型企业的技术工具,从事设计、编程、写作、咨询或贸易。这极大地降低了对传统资本和组织的依赖,为个体独特性的彰显与价值实现开辟了前所未有的空间。对当下的年轻人而言,重要的或许不再仅仅是寻求一份稳定的雇佣职位,而是如何在同质化竞争愈演愈烈的环境中,敏锐地识别并持续培育那份真正属于自己的、难以被算法和他人复制的独特优势。
在碎片化的角色扮演中对抗“异化”
2023年,一则“北京名校硕士辞去光鲜工作,返乡经营生态农业年收入超百万”的报道在网络上广泛传播,激起了无数都市职场人的共鸣与遐想。这一现象并非孤例,它折射出日益强烈的社会情绪:对高度异化、内卷化职场生活的倦怠,以及对重掌生活自主权、恢复劳动与生活直接联系的深切渴望。这种“逆向流动”的选择,可被视为个体对现代性困境的一种主动回应与实践性突围。
要理解这种集体性的焦虑与出走冲动,卡尔·马克思在一个多世纪前提出的“异化”理论依然闪烁着穿透时代的光芒。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深刻剖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者的生存状态。在前现代的生产关系中,一个手工业者或自耕农相对完整地掌控着劳动过程:他决定工作的节奏、采用的方法,并直接占有最终的劳动产品,劳动与人的本质力量展现存在着直接的统一性。
然而,在现代化的雇佣劳动制度下,劳动者被剥离为纯粹的生产要素,其劳动过程从属于资本意志,劳动产品作为异己的力量与劳动者对立,劳动本身也从目的降格为谋生的手段,这便是马克思所揭示的劳动的四种异化形态: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相异化、与劳动过程相异化、与人的类本质相异化,以及最终导致的人与人关系的异化。
具体而言,现代社会的异化主要表现为两种相互关联的维度。其一是劳动者相对于其劳动产品的异化,即工人不再拥有或支配自己创造的产品,其价值实现完全依赖于市场的交换与资本的认可。其二是更深层的劳动者与自身劳动活动及类本质的异化,劳动不再是自由自觉的创造性活动,不再是人的第一需要,而沦为维持肉体生存的被迫性苦役。
卓别林在电影《摩登时代》中扮演的那个被流水线节奏逼至疯狂的工人,正是工业时代异化劳动的经典写照;而今天,许多写字楼里的“知识工人”虽不从事体力劳作,却同样感到自己如同庞大系统里的一颗螺丝钉,从事着片段化、去技能化的工作,难以从工作中获得完整的意义感与成就感。
面对产品异化的问题,市场经济体系在实践中演化出若干旨在重新建立劳动与回报关联的机制。对于生产流程标准化、产出易于计量的岗位,计件工资制允许劳动者通过调节自身努力程度来直接影响收入,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其对产出的控制感。对于产出难以直接量化但对组织绩效至关重要的角色,如高级管理者、核心技术研发人员,股权、期权等长期激励工具被广泛采用,旨在让这些关键人力资本的所有者能够分享企业成长的剩余价值,从而将其个人利益与组织长远发展深度绑定。
此外,构建奖励正向行为的制度文化也至关重要,即通过清晰的规则设计,使对社会或组织有利的行为能够获得相匹配的回报。中国男子足球职业化改革多年却成效不彰,其深层症结之一便在于激励结构的扭曲:当俱乐部所有者发现通过操纵比赛(赌球)所能获得的短期收益,远高于苦心经营俱乐部所带来的长期资产增值时,他们自然缺乏建设健康足球产业的真正动力。
相较之下,应对“自我异化”则是一项更为复杂和内在的工程。现代性的一个核心特征是社会角色的高度分化与场景化切换。同一个人,在家庭中是承担责任的父母或子女,在职场上是执行指令的下属或发布指令的上司,在社交网络中是精心经营形象的表演者。我们不断地在不同角色模板中穿梭,适应着迥异的行为规范与期待。这种角色分化本身是社会复杂化的必然产物,并非必然导致异化;真正的危机在于,个体在这些碎片化的角色扮演中,可能逐渐丢失了那个内在统一、自我掌控的“核心自我”,感到自己像一个被外界剧本驱动的演员,而非自己人生的编剧与主角。
人工智能与人类宿命:当工作不再是生存必需品,我们何以自处?
202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罕见地授予了在人工智能基础理论领域做出开创性贡献的两位学者,这一标志性事件被广泛解读为科学共同体对AI技术革命性意义的至高认可。随着ChatGPT、Sora等生成式人工智能以惊人的速度迭代进化,其展现出的内容创作、逻辑推理乃至初步的理解能力,使得“机器替代人类工作”这一长期议题从未来学讨论急速逼近为眼前的现实挑战,迫使全社会必须严肃思考一个看似遥远却迫在眉睫的问题:如果大部分传统工作终将被AI胜任,人类的价值与意义将安放于何处?
回溯人类文明演进的长河,其主线之一便是不断发明并利用工具来替代和增强自身的体力与脑力。从旧石器时代的打制石器到农业时代的畜力与犁具,从工业革命的蒸汽机、电动机到信息时代的计算机与互联网,每一次重大技术飞跃都在重塑劳动形态、解放人类部分机能。然而,以深度学习为代表的新一代人工智能的颠覆性在于,它首次在诸多领域展现出大规模替代人类复杂认知工作的潜力,包括但不限于文本处理、数据分析、艺术创作、代码编写乃至部分诊断与决策。这触及了人类长期以来引以为傲的智慧高地,从而引发了更深层次的生存性焦虑。
这种对技术替代的忧惧并非新鲜事物。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洋务运动时期,清朝首任驻英副使刘锡鸿在考察英国后,虽对火车、电报、印刷机等新技术成果赞叹不已,却在奏折中坚决反对将其引入中国,其核心理由便是忧虑这些高效机器会“夺小民生计”,造成大量挑夫、驿卒、抄写员失业。这种基于社会稳定的保守考量,与今天许多人反对人工智能的底层逻辑惊人地相似。然而,历史反复证明,技术的洪流不会因部分人的担忧而转向,文明进步的齿轮总是朝着提升整体生产效率与可能性的方向转动。
从更宏大的宇宙观视角审视,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宇宙作为一个孤立系统,其熵(即无序度)总是在增加,最终将走向热寂。而人类文明,作为一个局部的、暂时的系统,却在进行着艰难的“熵减”努力——我们通过科技与组织,将分散的能量与物质转化为有序的结构、产品与知识,创造出一个个局部有序的“绿洲”。人工智能,或许是人类在这场对抗宇宙熵增的永恒战役中,迄今为止所获得的最强大的工具之一。它的意义不仅在于解决当下的生产效率问题,更关乎人类长远的生存与发展,例如应对气候变化、探索宇宙深空、破解疾病密码等宏大挑战。
当AI承担了社会中大部分程式化、重复性的生产与服务职能后,一个“后工作社会”的图景或许将逐渐浮现。届时,社会将面临两大根本性转向。
其一,劳动的性质可能从“生存必需”转向“意义实现”。人们可能更多地为了兴趣、创造、社交或自我完善而从事活动。然而,心理学研究提示我们,纯粹依赖内在动机的活动,若完全缺乏外部认可与社会性反馈,其持久性往往面临挑战。
其二,社会可能需要重新定义“分配”与“保障”机制。近年来,一些思想家与经济学者提出的“全民基本收入”构想日益受到关注,即通过对人工智能、自动化技术所带来的超额利润征税,为社会每一位成员提供一份无需条件的基本收入,确保其物质生存底线。
在此基础上,个体得以从生存压力中解放出来,自由探索教育、艺术、社区服务、科学研究等多样化领域,寻找自身热情所在,发展独特潜能,从而在一个物质丰裕的时代,重建劳动与人生意义之间的有机联系。
面对算法无所不在的精密计算、社会竞争不断内卷化的巨大压力,以及人工智能带来的未来不确定性,当代人普遍体验着一种深刻的迷茫与焦虑:在外部规则日益复杂且强力的时代,个体如何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与主动的姿态,真正“活明白”?外部的系统与算法或许强大,但我们内心解读世界、回应挑战的“算法”却始终保有可编程的空间。






